取劍:阿鼻劍前傳連載之第十七回
C 出版M 漫畫與小說P 隨筆
【取劍:阿鼻劍前傳連載之第十七回】
我進了城。時近中午。
回來取劍。
這是那夜從星空回到現世之後做的決定。
人生前程,朦朦朧朧的心思都清楚了。就是要跟嬋兒一起。
活著有了最大的想頭,但也有了恐懼。
我何其幸運,能把老虎活活殺了,保護了嬋兒。但那是太多凑巧。人世的凶險,老虎還算小的,不能總靠運氣。
我也想起那些淪落的流民。比起他們,我也沒有好多少。想到這,心頭像是拉開一個口子,口子裡有個聲音:就憑你也想保護嬋兒?
如果手裡有一把劍的話,就不同。
再說,殺了老虎之後,我覺得整個人不一樣了。天下事,好像再沒什麼好怕的。
所以,想回城裡一趟的心思,是老虎嚇出來的,也是牠給了我勇氣。
這樣,就在中秋的晚上,我趁他們入睡,半夜自己摸黑下山。
到了城外,天已經大亮。我遇上一家人歡天喜地迎親,省了盤算怎麼混進城去,夾在人堆裡就進去了。
照過去的經驗,衙門裡的人,總有人奉承,每天都請吃請喝,經常大白天就有人醉醺醺的。那天在牢裡聽他們說話,該是常去一家「大吃家」,那位二哥迷上了飯館裡的什麼人。
記得在我住的那家客棧隔壁,就有家飯館張著這個旗號。進城沒多久就找到。
「大吃家」對街的角落,已經蹲了七、八個叫花子。客棧、飯館外頭,常有人這麼等著。有時候店主大發慈心,會把剩菜拿出來施捨。我把頭臉弄得髒亂一些,也過去蹲著。
料得沒錯。
晌午的時候,一夥人來了。都是捕役衣著,喳喳呼呼的。路上的人能閃的都躲開。那個叫二哥的大塊頭,正帶頭走在前面。他腰上別的,劍鞘暗紅,正是我那一把。我心頭一陣亂跳,五味雜陳。
他們到了大吃家門口,有人出來殷勤招呼,只聽一陣客套和「恭喜」之聲。可等一下怎麼把劍搶回來呢?我本來想好的路,這時只覺都走不通。
蹲在那裡發愣的當兒,大吃家有個女人出來,吆喝著放了兩個碗在地上:「朱大爺慶壽,賞你們吃的。還不快來謝恩!」
要飯的一哄而去,朱大爺朱大爺的叫嚷著。
我雖然肚子也餓了,可也不想去搶那些剩菜殘羹。一個人蹲在那裡也不是個辦法,就起身走走,等他們快吃好了的時候再回來。
朝捕役來的方向沒走多久,就看到衙門。
門口立著「肅靜」、「迴避」兩大塊牌子。再走近些,門口守著一個人,剛吃好飯的樣子,在剔牙。他朝我看了一眼,剛瞪起眼要叱喝什麼,卻露出一個奇怪的表情又沒出聲。
這城裡路上人也不少,剛才迎面過來幾個人,也有那表情。這次我順著那衙役的表情回頭望了一眼。
身後七、八步,悄悄地站著一夥人,正是剛才去大吃家的那幾個。叫二哥的站在頭裡。他們一路沒出聲,看到我發現了,幾個人快速散開,封住我去路。路上看熱鬧的人也都擠過來。
一名衙役說:「二哥,你的眼力真好。真是這小子。」
二哥說:「現在差多了。沒叫老闆娘出去試那一下我還不敢確定。」他笑咪咪地踱向前:「你真好大的膽子,怎麼敢回來?」
我腦子有些轟轟的:「把我的劍還我。」
二哥愣了一下,看看自己腰間的劍,哈哈笑了:「你為了這個回來啊。」回頭朝身後一人說:「朱大爺,這裡也有個愛劍的人呢。」
朱大爺三十來歲,長得人模人樣,一身綢緞,今天過生日,臉上更帶著喜氣。這時我注意到,他這個壽星今天腰間也佩著一把劍。
我悶得有點難受:「我的東西,還我。」
二哥哦了一聲,沒理我,回身走過去跟朱大爺附耳交談了一陣又回來。
「這樣吧。」他說:「你這個江洋大盜,上次有人劫法場,逃過一命。這次回來,理當馬上把你拿下。可是呢,」他再轉頭看看:「幸好今天朱大爺慶壽。他平日就愛劍,也是使劍的名家。剛才我跟他商量過,你陪他走幾招,能贏了他,就把劍還你。如何?」
這不必想就可以回答:「當然好。那在哪裡?」
二哥說:「咱們都到了衙門門口,就到裡面去,在院子裡。」他看我的表情,又加了一句:「只要你贏了,我開大門送你出來。」
「說話算話?」
「我王風說過的話,這城裡哪個人不知道鐵板釘釘?」他說到後面那句特別揚高了聲音,還張望了四下。「大家幫我作個證吧。」
他那些兄弟帶頭響應了聲:「好。」
四周一陣喧譁起鬨。
我的膽氣大增,也說:「好。」
王風說了句:「請。」
然後我就走進了衙門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–
上一篇:【星空之下:阿鼻劍前傳連載之第十六回】下篇
http://bit.ly/38ZxK8D
下一篇:【過招:阿鼻劍前傳連載之第十八回】
如要討論,歡迎加入 阿鼻劍社團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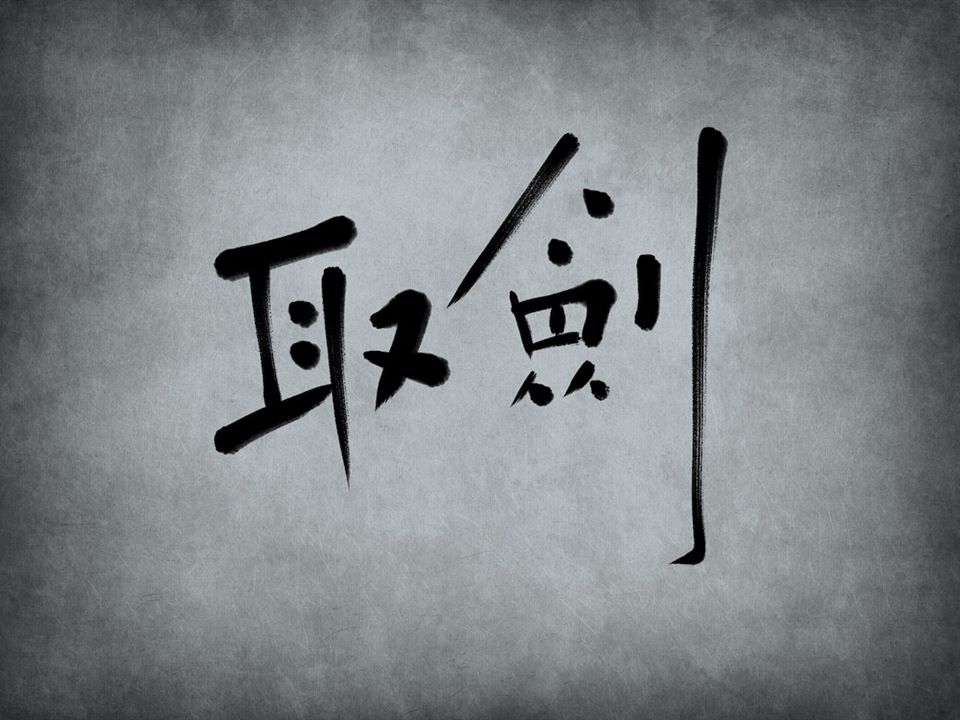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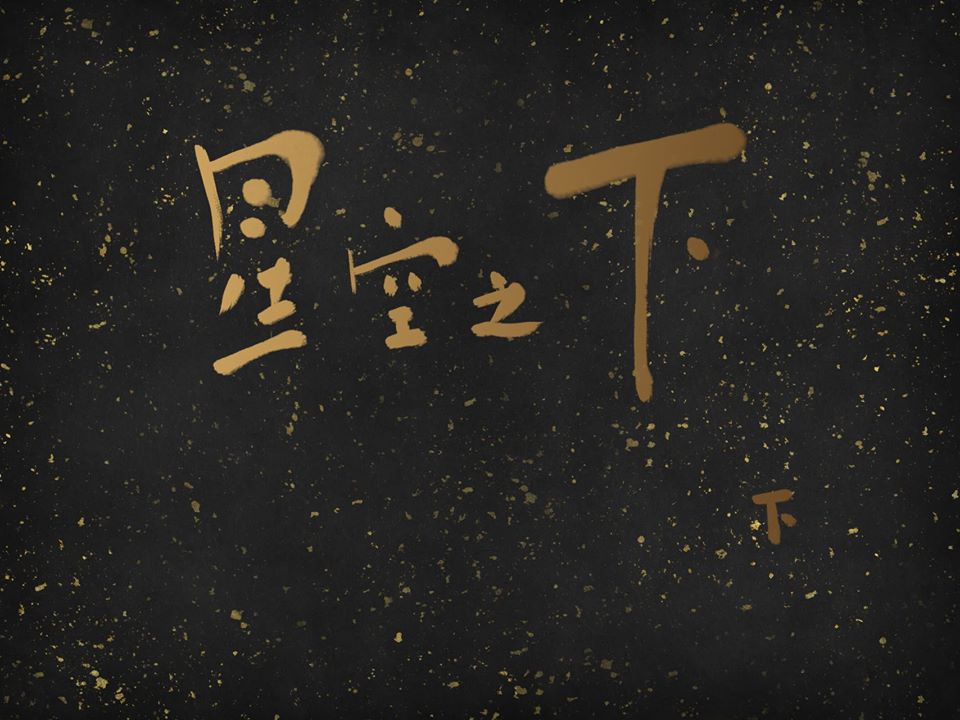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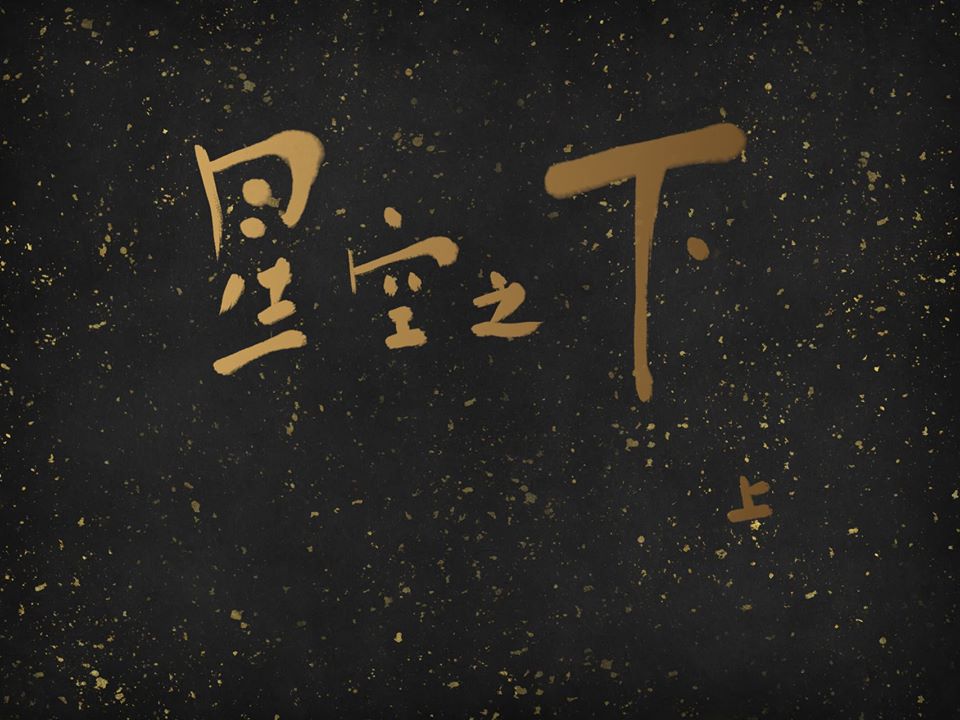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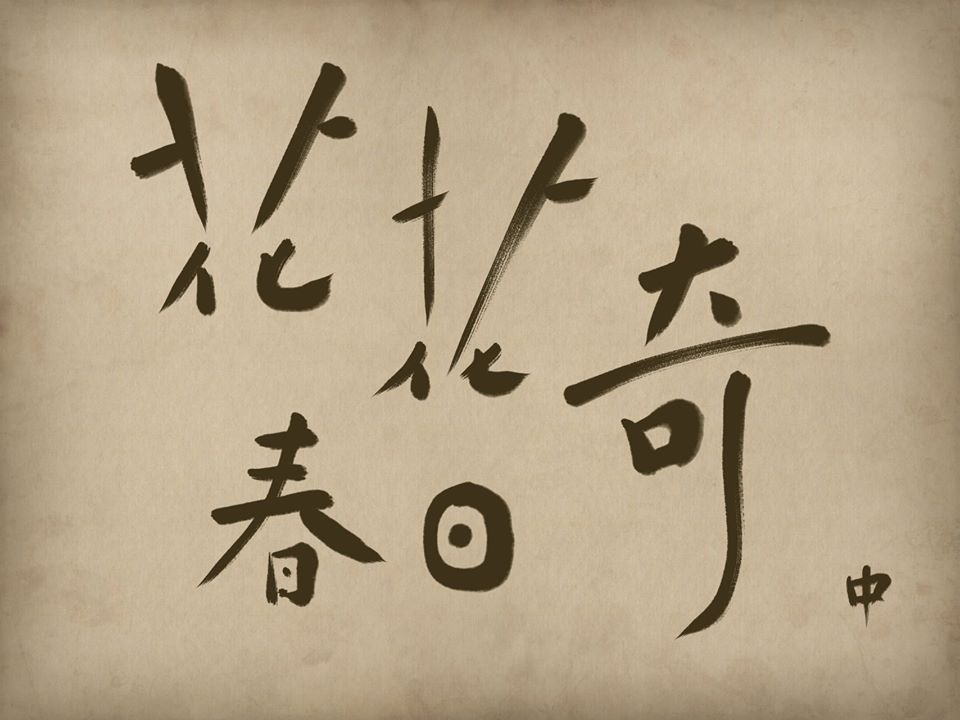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