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(下)之二 (文字版)
B 閱讀C 出版G 政府與政治K 健康/醫療/社會P 隨筆
第 18 集 當臺灣遇見疫情 (下)之二 (文字版)
最後,我們來談:在疫情時代,我們為什麼要勇敢地夢想。
1.
林益仁教授和劉紹華教授都提到:在 2020 年復活節前夕,教宗在空無一人的廣場發表了一份文告。
在《讓我們勇敢夢想》這本書裡也提到這件事,說教宗在發表那份文告之後, 回去就採取了行動。他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,開始針對疫情之後的世界,未來的世界,要採取行動。
林益仁教授說:重點應該就是教宗在書裡所說的,他所關切的「土地」、「居所」、「勞動」這三個課題如何實踐得更美好。
劉紹華教授說:看教宗的行動,他未來的計劃的格局是非常大的,有如當年聯合國設立的時候的理念一樣。
而今天雖然很多人批評聯合國的組織 ,但它畢竟還存在,並且有人還繼續維護它的存在。為什麼呢?因為設立聯合國的那些理念是非常崇高、美好的。
不應該只是為了一些組織上、技術上的問題,就完全否定那些理念存在的價值。
因此劉紹華教授提醒我們:我們應該放大格局、拉高目標。
因為放大了格局、拉高了目標,揭櫫美好的願景之後,
就好像把傘給放大了、擴大了。
當傘變大了之後,下面可以容納的差異性也就跟著變大。
2.
那怎麼把自己的格局放大?怎麼把自己的願景拉高?
劉教授認為教宗在書裡講的一點非常重要。
那就是必須從自己出發,去中心化。
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夠超越自己,
把緊綁住自己心智的利益給鬆綁,那我們就比較可能容納別人的利益進來,
就會比較容易有整體的格局,不只會看到自己、社會、國家的格局,
也可以看到一種全球的格局,把全世界的人、事、物,各種生物都一起納入,
朝那個目標共同努力的格局。
劉教授說,這也是世世代代有遠見的人、有先知的人都在告訴我們的事情,
告訴我們人類應該走向那個美好的願景。
只不過我們經常因為短視,或者是因為身邊小小的利益,或者是我們自己的一些人際網絡 就忘記了這一點。
因此她認為就像教宗在書裡面所說的,我們需要一直提醒、喚醒大家。
劉紹華教授說:有許多事情看起來很大,是全球性的問題,像是必須政府領袖級的人才關心得到的問題 ,但事實上 只要每個地方有更多的人被喚醒,就可能去改變自己政府的決策;而只要有愈來愈多地方的政府改變一點決策,那這個世界也許就是有希望的。
3.
最後,劉教授還提醒了一點很有意思的事。
她說:臺灣一直想加入聯合國,但是每當談到聯合國這些美好的目標的時候,
我們卻又會說:我們還不是聯合國的成員。
所以,她說:如果我們不學習這種全球性文明的語言跟姿態,等到有一天突然運氣好了,
人家邀請我們成為聯合國的會員的時候,我們到底要講些什麼呢?
怎麼和人家談判、協商 、溝通?
怎樣才能夠既知道爭取自己的利益,也爭取世人的利益?
否則,很可能人家讓你成為會員,讓你上台發言,你也會啞口無言,
或者跟人家講的話是失態的。
我對劉教授這段話深有所感。
就像之前趙家緯教授所說的,
在去年當全世界都在防疫的同時,也在注重減碳、排碳的當兒,
我們臺灣卻是燃油機車賣的最多的一年;
我們是是用超低的電價供應工業用電,造成臺電用電創紀錄的一年。
其他國家為了減碳,要求航空公司減免短程航班的時候 ,
我們全國卻在熱鬧地享受「偽出國」這種短程航班。
我們一直感嘆臺灣沒有受到國際的注意,也一直急於讓世界看到臺灣,
但是和我們這些渴望的意念相比較起來,我們所該有的準備也是差了一大截的。
這件事一方面可以當成我們的警惕,另一方面其實也可以當成我們的鼓勵。
因為如果我們當真學習到了這種全球性的語言和姿態的話,
其實我們是不用擔心別人看不到我們的。
4.
從 2003 年的 SARS,到 2020 年的 SARS 2 號病毒,其實病毒一直都在提醒我們一件事情—-我們人類要謙虛。
所以像我們臺灣,去年疫情開始的時候就勤於戴口罩、勤洗手,那是懂得謙虛,是有福的。
但是等我們自以為這樣做就是全部的時候,疫情的破口就來了。
同樣的,歐美各國一直在等待疫苗。
但顯然,光是相信疫苗是不夠的。
像以色列這個疫苗覆蓋率如此之高的地方,現在疫苗的效力正在巨幅下降。
或者像美國,美國現在已經在考慮要打第三劑來當成一種標準措施。
這樣看的話,經過前面所有的探討,還有許多學者專家的意見,我們其實可以知道兩件事。
首先,就是臺灣經過了去年持續的「加零」領先全球的成績之後 ,
今年疫情有了破口,其實是禍中有福。
因為如果沒有爆發今年的疫情,我們就會更會自以為是地 ,
只以為封閉邊境、勤洗手、戴口罩就是全部,對許多更根本的問題視而不見。
不要忘記:在今年 5 月之前,不論政府還是社會上的許多人,曾經對疫苗這件事情有多麼不放在心上。
第二,是雖然 5 月之後的疫情現在又大幅改善,
可是我們不能又以為這就表示我們可以回到過去的「常態」,
或者又開始追求「加零」的成績,對其他視而不見。
5.
有人也許會問:我們努力追求「加零」有什麼不好?
為什麼一定要說,還要對許多根本問題必須要改善?
我想到一個比喻。
這就好像父母在問:「我要孩子每一科都考一百分,這有什麼不好?」
孩子應該是身心均衡成長,然後自然出現好成績。
如果父母只要求孩子一直只考一百分,卻不顧他身心的平衡發展,
那這種一百分是不可能持久的,並且孩子總有一天會爆發更大問題的。
防疫也正是如此。
如果我們不顧公共衛生、弱勢族群、生態環境、政府和公民社會應該有的運作,
而只是用封閉邊境、洗手、口罩來控制疫情,
一旦確診人數升高就管制移動,進行自保、獵巫,對別人污名化,
那這也是不可能持久的。並且一旦升高,就會爆發更大的問題。
那到底要怎麼改善?
我們應該要求政府進行各種改善,也更應該自己就採取行動。
知道從自己開始,讓自己關心的事情不只是疫情,而是把疫情當作是一個起點。
讓自己去中心化的起點。
開始關心自己過去不關心的事情,尤其是覺得離自己很遠的社會邊緣的事情。
一旦我們願意出發,去看邊緣,去抵達到邊緣,
那自然會知道自己還可以做些什麼事,
然後讓自己勇敢地夢想,期許自己成為一個更美好的人。
「讓我們勇敢夢想」十八集專題到此告一段落。 謝謝大家的收聽和收看。
也非常感謝這段時間所有接受我訪問的專家學者,以及協助我製作完成這個專題的朋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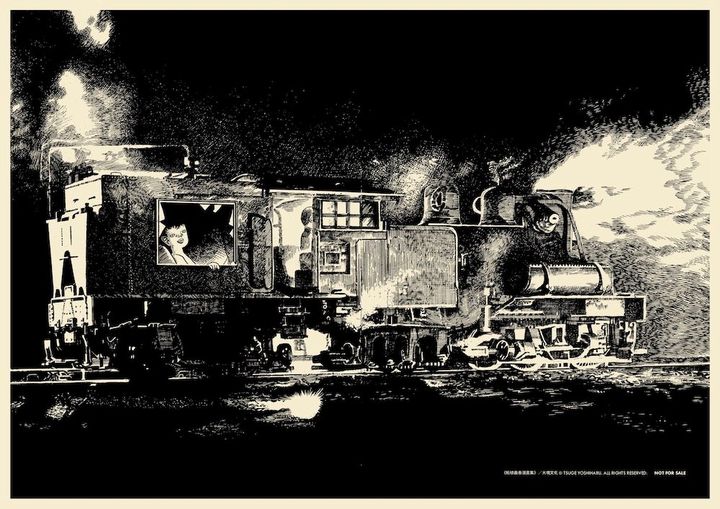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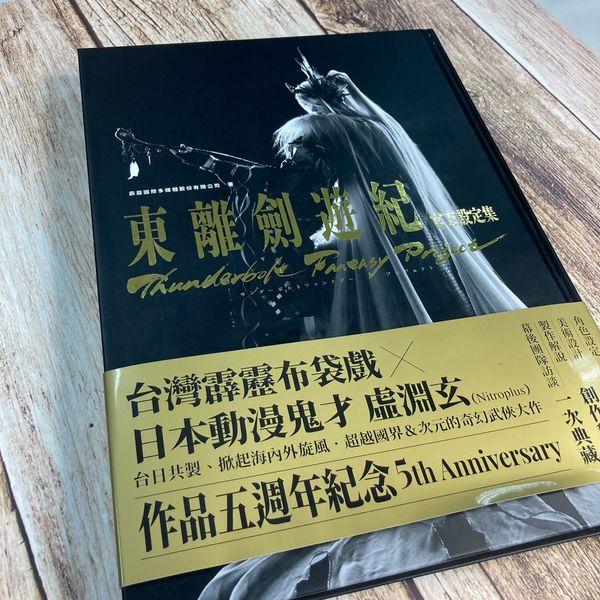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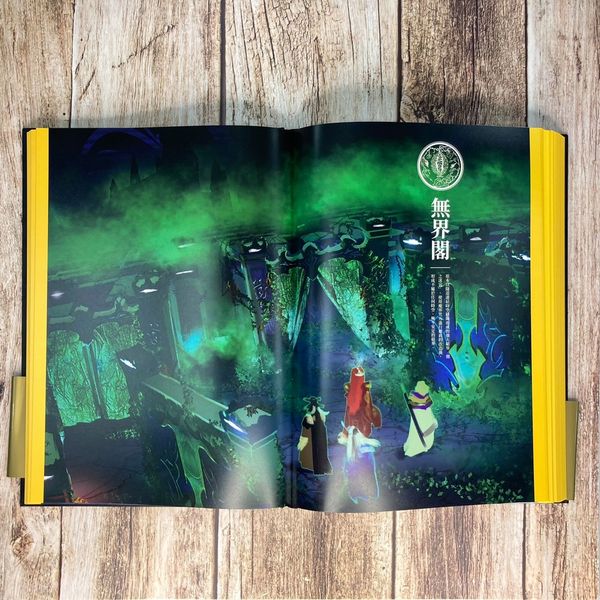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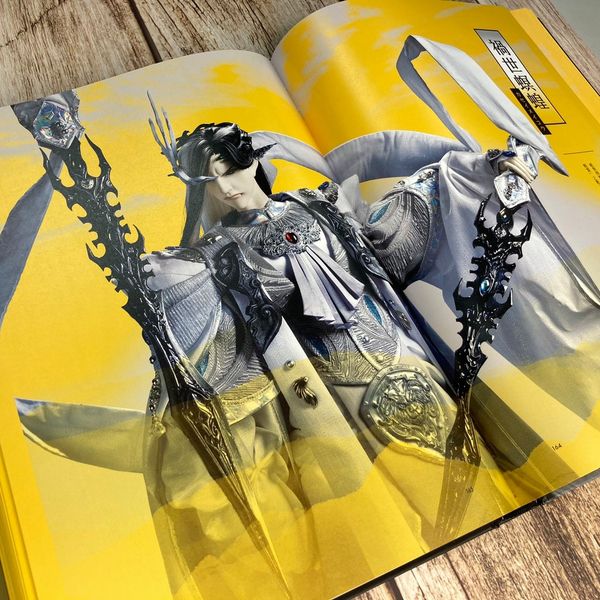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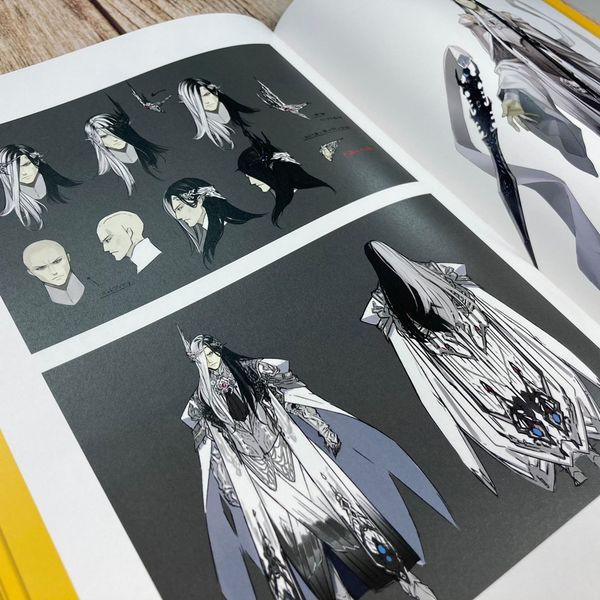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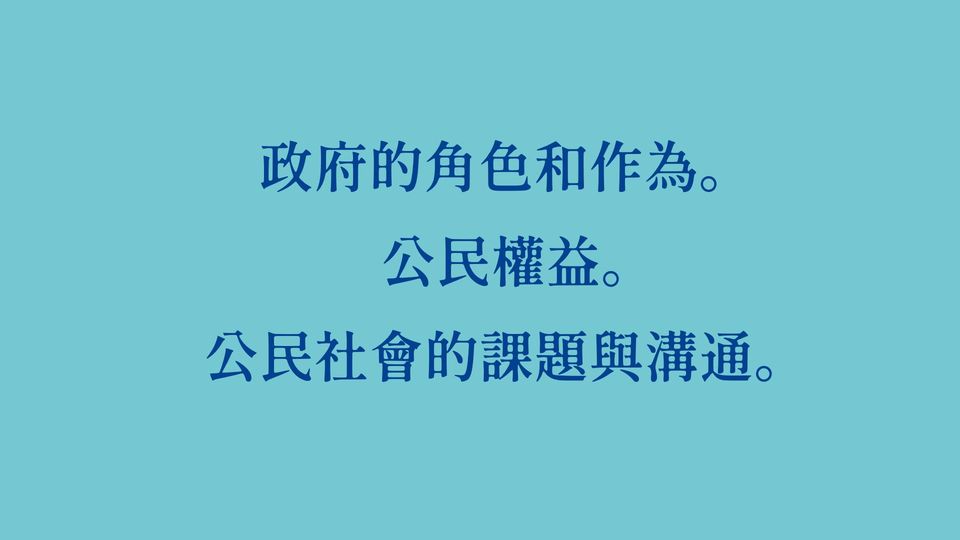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