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8 年 10 月 25 日,20:51
F 文化相關P 隨筆
【會於太平洋之濱】
張卉君 Hui-chun Chang 聯絡我,說「黑潮」二十周年,規劃了一系列的講座與活動,邀我去花蓮講一場。
我認識卉君,是三年半以前我著手寫《如果台灣的四周是海洋》,看到報紙上有個女孩子在花蓮當鯨豚導覽,感到好奇而結識。
卉君自己的故事就是很澎湃的海洋。一個台中女孩子,到台南讀大學,去中國雲南、哈爾濱、內蒙等地流浪,再回到花蓮定居,在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工作,後來再接任執行長。
我去花蓮找她,也跟她出過海去看鯨豚,再出版了她寫的《黑潮洶湧》。
卉君的外號是「洪亮」,取自她歌唱的聲音。她幫我不只補了許多海洋知性的課,引發我對海洋感性的想像,也因為她積極參與公民行動,從花蓮向全台灣其他各地連結,所以講話有很多金句。
譬如說,「過去,人民是被逼上梁山。現在,我們是被逼當公民。」張卉君這麼說,「越來越多人不相信政府,越來越多人不相信政治人物,連拜託立委也不需要。在議題上,每個人都是守門人,每個人都不能缺席。」
10月28日(星期日)下午四點,在花蓮市的松園別館,我會去講一場「年輕世代與海洋思維」,一方面祝黑潮20歲生日快樂,一方面也和花蓮的朋友交流,聽聽九合一大選在即,花蓮的「國王」也已經入獄的此刻,他們對被逼得當公民的現實又有什麼新的看法。
就讓我們在太平洋之濱會一會。
花蓮的朋友,周日見。
相關閱讀:
【浪遊世界又回到海上的女孩子】http://bit.ly/2Sfgip4
黑潮20周年頁面:http://bit.ly/2qbZZN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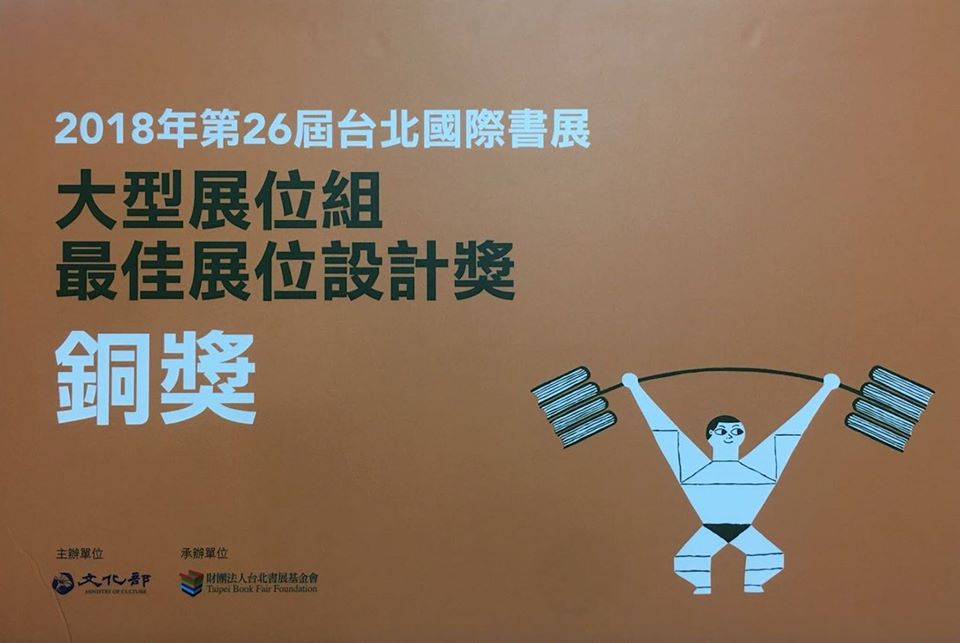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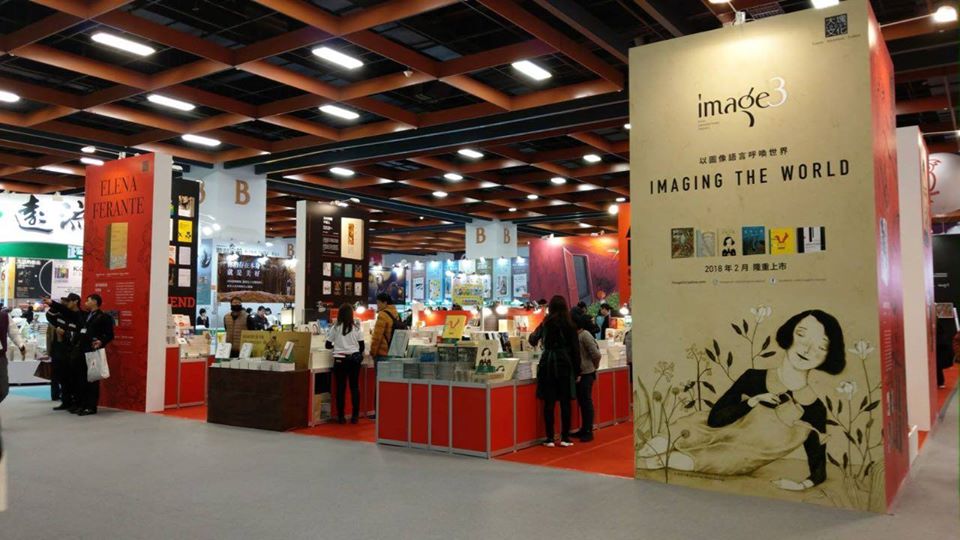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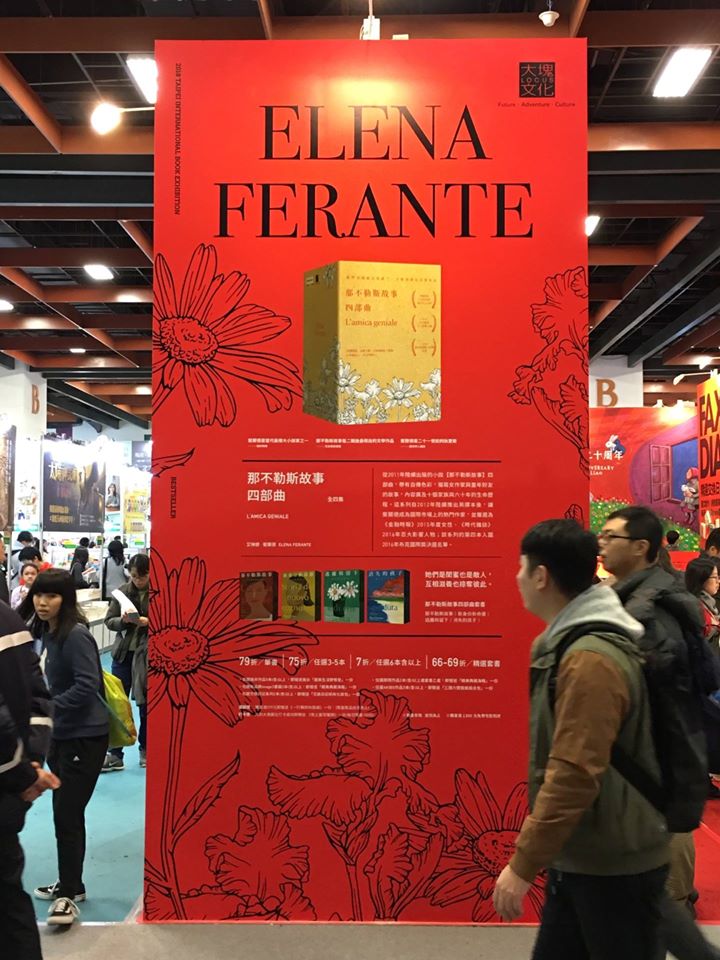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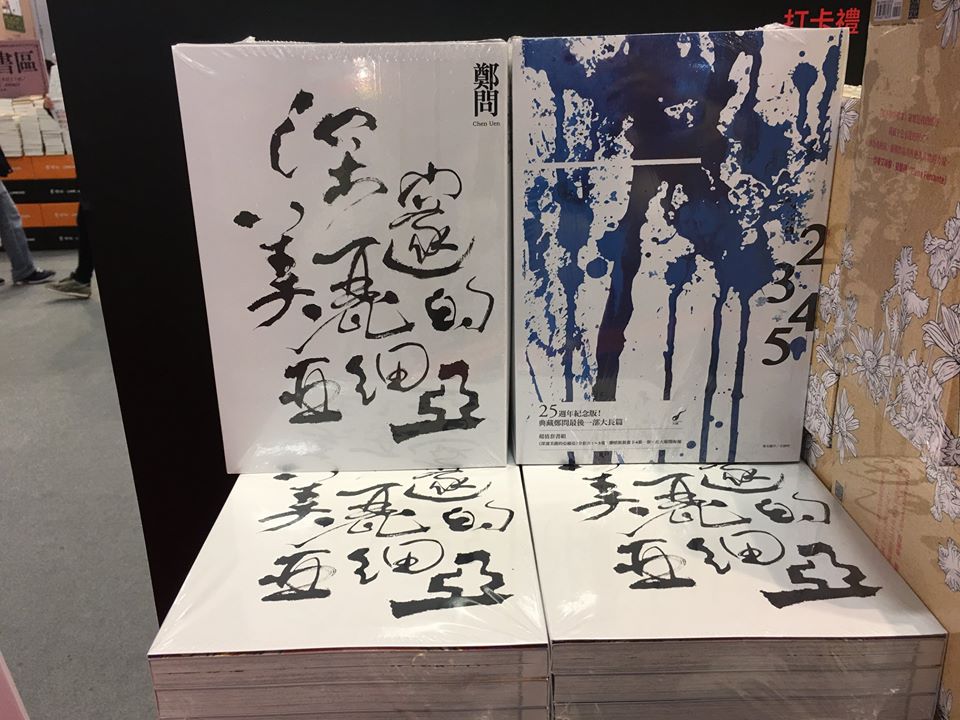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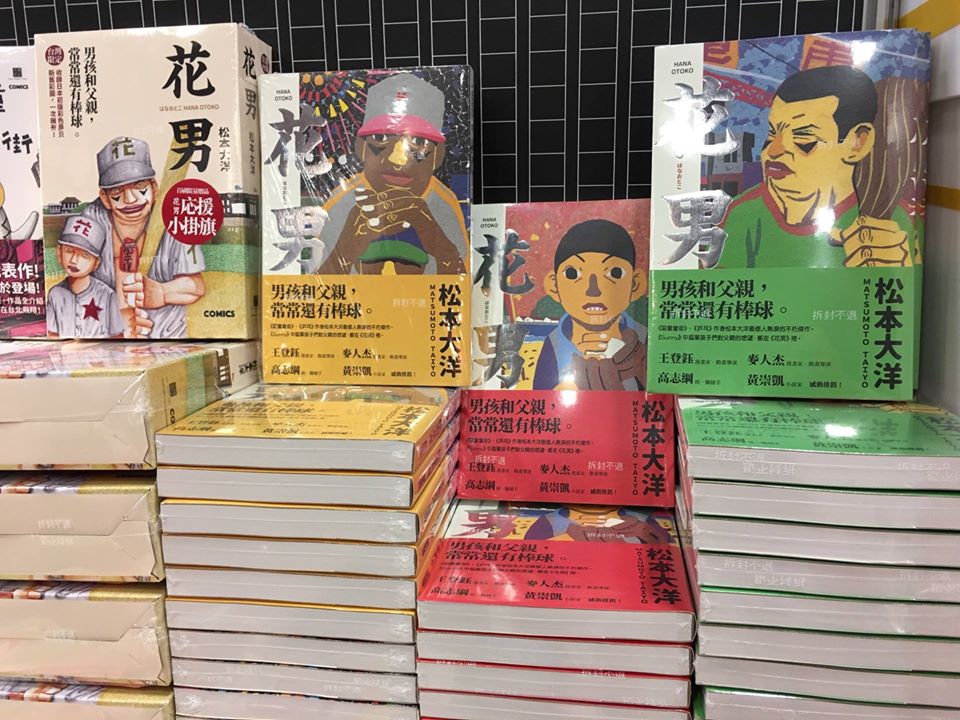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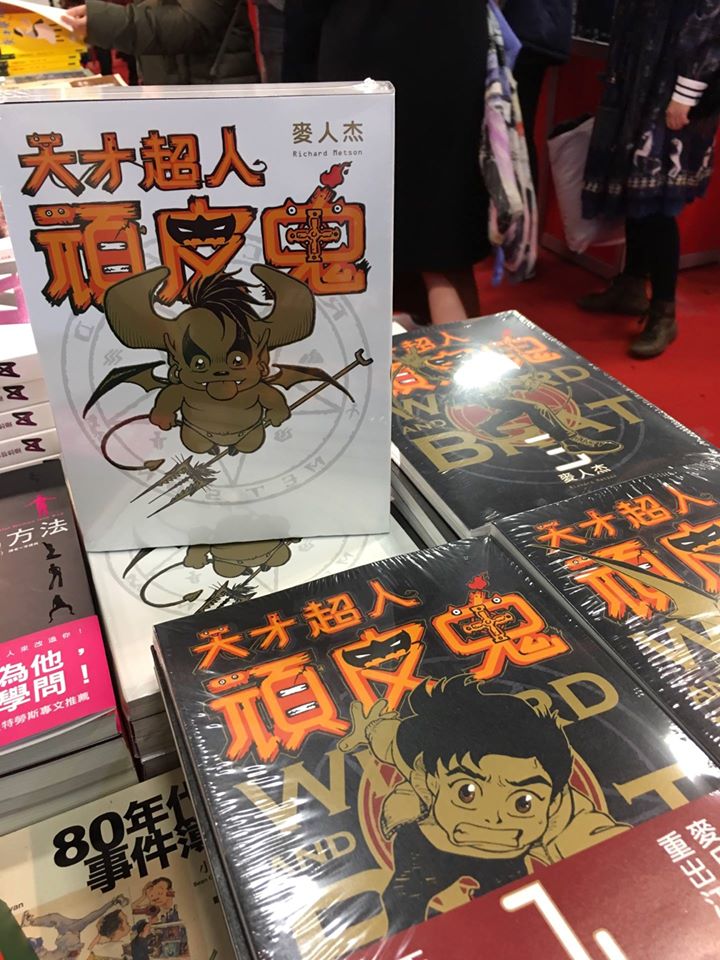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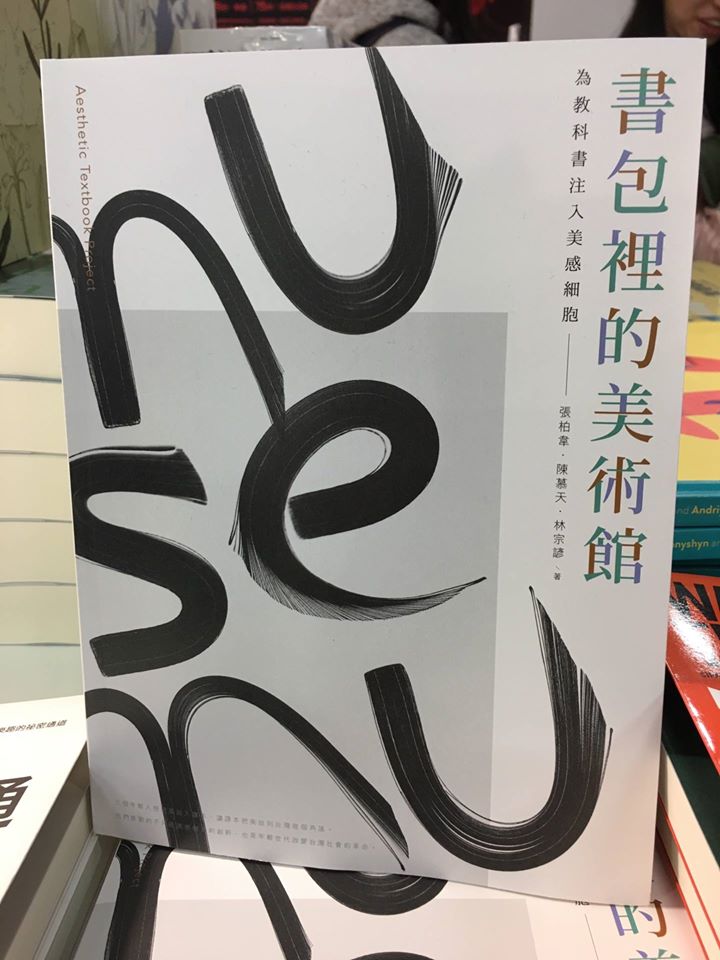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