應該問林飛帆的3件事
G 政府與政治O 活動與新聞報導P 隨筆
【應該問林飛帆的3件事】
林飛帆去民進黨當了副秘書長。
2016年初,上次大選結束後我訪問林飛帆,他談到三點。
第一,林飛帆說,『他自己很早就在想組黨這件事,覺得年輕人應該有自己的政黨,思考「我們年輕世代最優先最主要處理的議題該是什麼?我們是不是應該有自己的政治綱領,或者行動綱領?」』
太陽花學運結束之後,因為有些學運成員和他的意見不同,所以此事沒有發生。
第二,對於那次大選的結果,林飛帆說『他認為學運的力量是被民進黨收割了。』
我問他這對學運世代本身的意義是什麼,他說:『我們的時代還沒那麼快到來吧。』
第三,對於學運世代如何參與2016年那次大選,林飛帆的主張是:『本來,搞運動的時候大家一起搞,到後來介入政治,參選的時候,大家也應該形成集體力量。譬如我們這個世代的人就都投入民進黨,或是都加入時代力量,或是都加入綠社盟。但是沒有,我們反而是各自行動。』
所以基於他說的這三點,應該問他的是三個問題:
一,時間又過去了四年,林飛帆為什麼認為年輕世代今天仍然還沒有等到自己的時代到來,思考自己的政治綱領或者行動綱領?為什麼反而去為已經代表既得利益的民進黨助陣?
二,他四年前感嘆『學運力量是被民進黨收割了』,那現在他是否更落實了自己當初的感嘆?
三,或者,他是因為想要實踐『應該形成集體力量』的想法,所以投入民進黨,期待從內部推動什麼改革?如果是,那為什麼沒有考慮進入時代力量形成集體力量?如果是,接下來他要如何號召更多的學運世代進入民進黨集體推動改革?做不到的話,豈不仍然是各自行動?
林飛帆也可以現在不必回答。將來時間會回答。
相關閱讀:
【訪問林飛帆】 http://bit.ly/2XSEuz4
【從林飛帆們錯過的事看2020大選 (下篇)】http://bit.ly/2wTbhcc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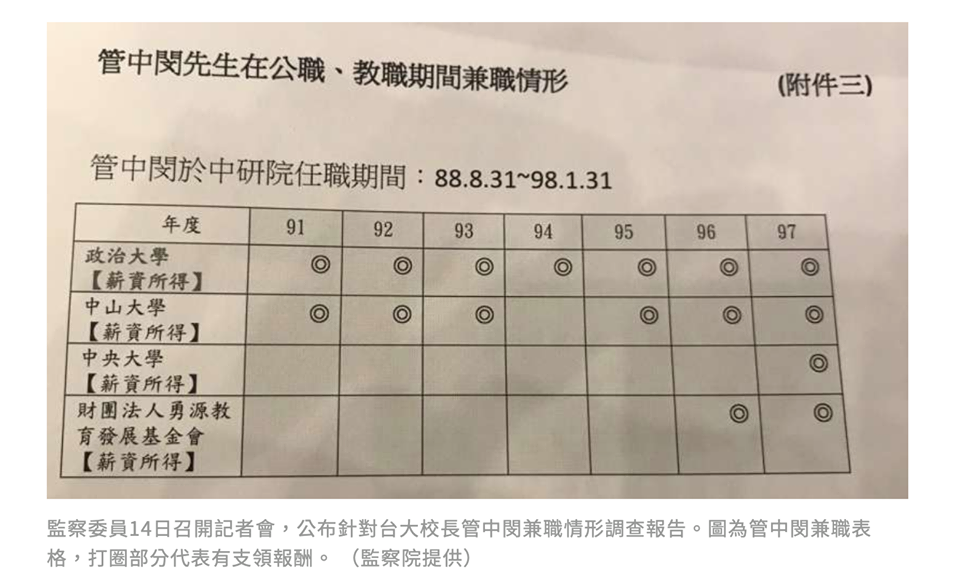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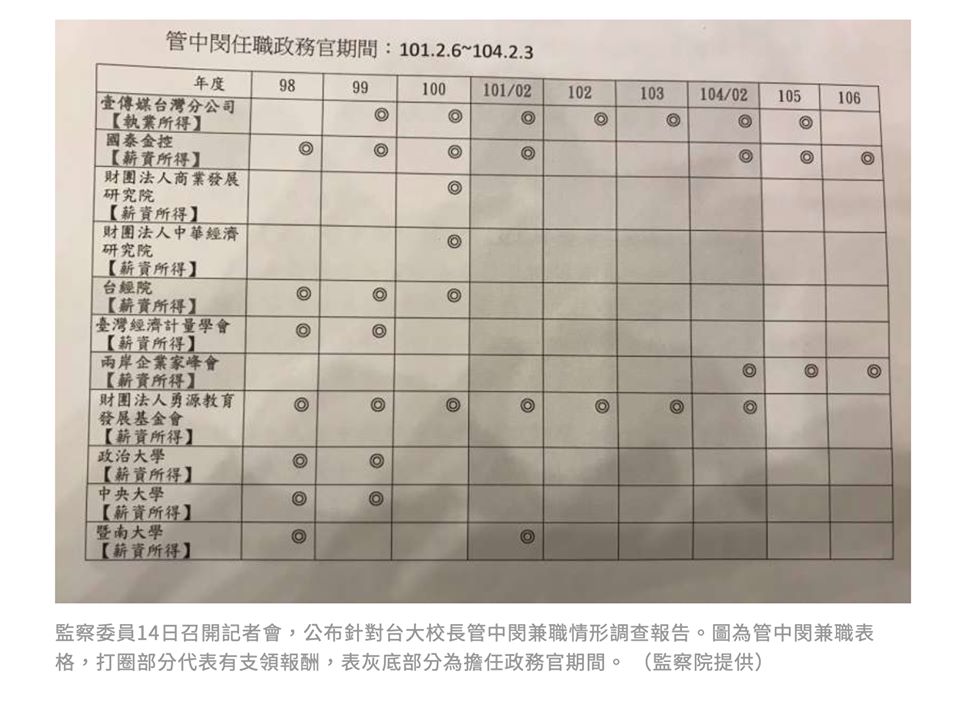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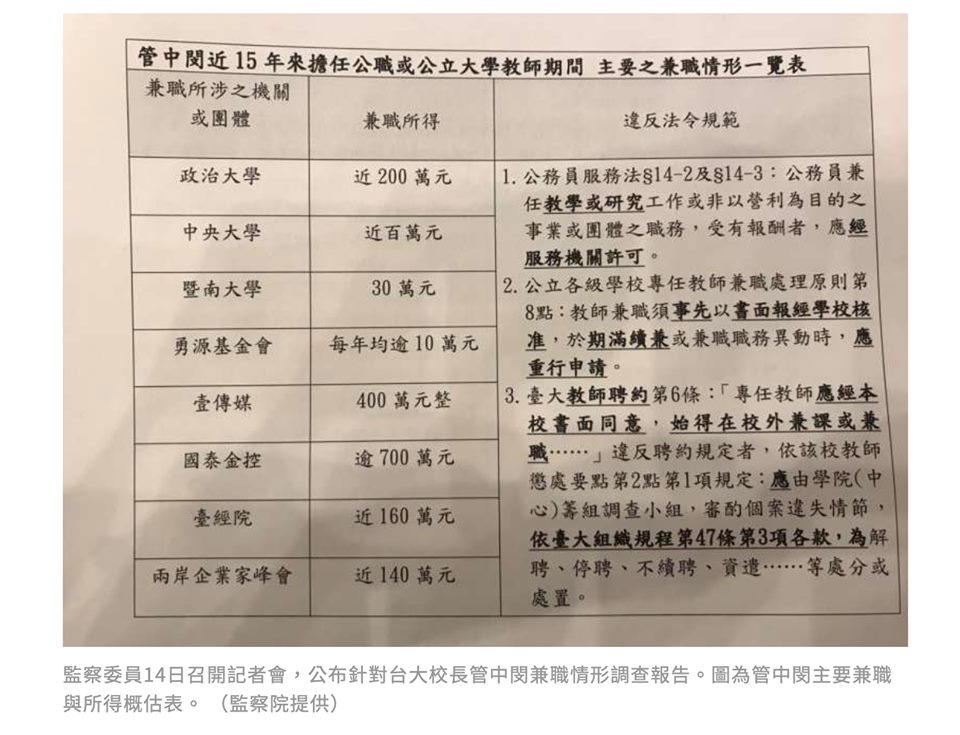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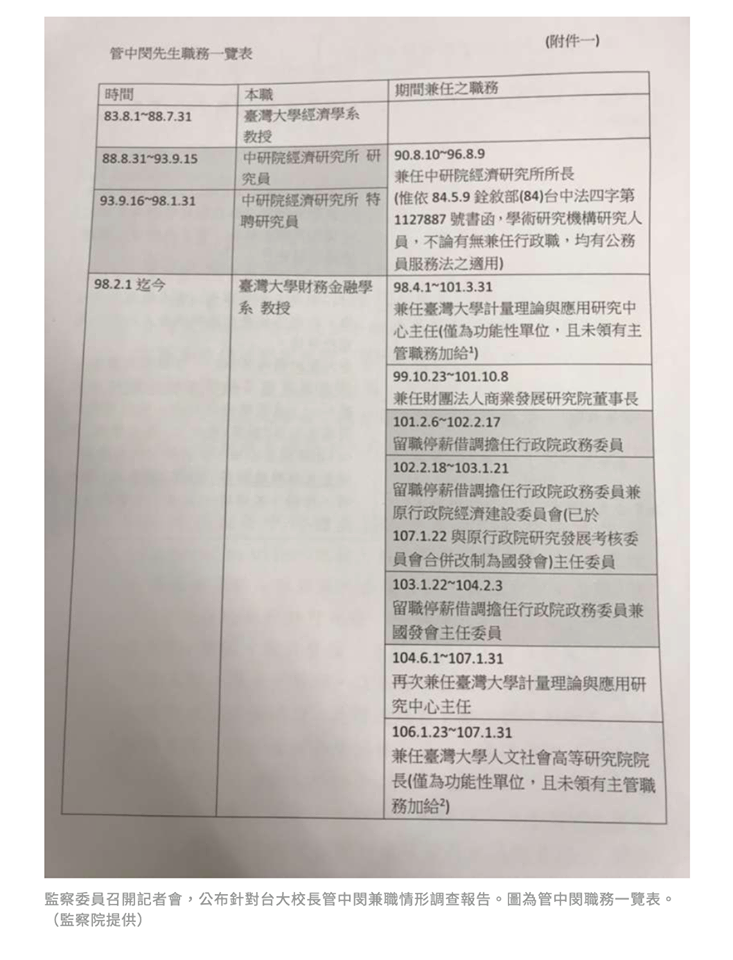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