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1 年 6 月 3 日,19:01
G 政府與政治K 健康/醫療/社會P 隨筆
劉黎兒今天發自東京的報導說:『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今天 (3日) 在日本參議院外交委會裡依然表示對台灣提供疫苗,因為台灣是有緊急迫切需要,而且台灣是在患難時必須互助的對象,因為這些都是在中國開始牽制日本之後的發言,顯見這次日硬起來了!』
給日本鼓掌!
但是同一篇報導說,『根據首相官邸高官表示「台灣是要求6月中旬之後再給,日本現在配合台灣要求在調整!」』
劉黎兒提出質疑:『AZ要給台灣,當然越多越好,而且也是越快越好,日本原本6月初就可送到台灣,不理解為何台灣要求「過了六月中旬」要延遲送台時間,差個10天或10幾天或許會差很多人命,可以減少確診者重症化及死亡,因此日本堅挺台灣,也希望台灣政府好好為台灣人爭取數量及時間!』
的確是。請政府說明一下為什麼要日本6月中旬之後再給疫苗的理由。
劉黎兒觀點》中國牽制無效 日本一心要給台灣AZ疫苗 不解為何要拖到六月中 | 政治 | 新頭殼 Newtalk
在中國外交部大批日本給台灣疫苗是干涉內政後,不僅首相菅義偉昨天公開表明會直送AZ疫苗到台灣外,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今天 (3日) 在日本參議院外交委會裡依然表示對台灣提供疫苗,因為台灣是有緊急迫切需要,而且…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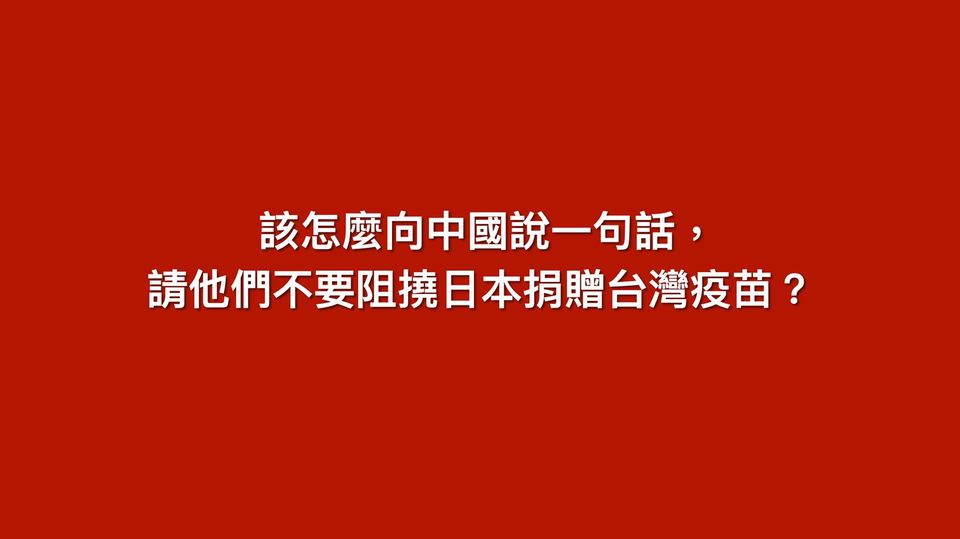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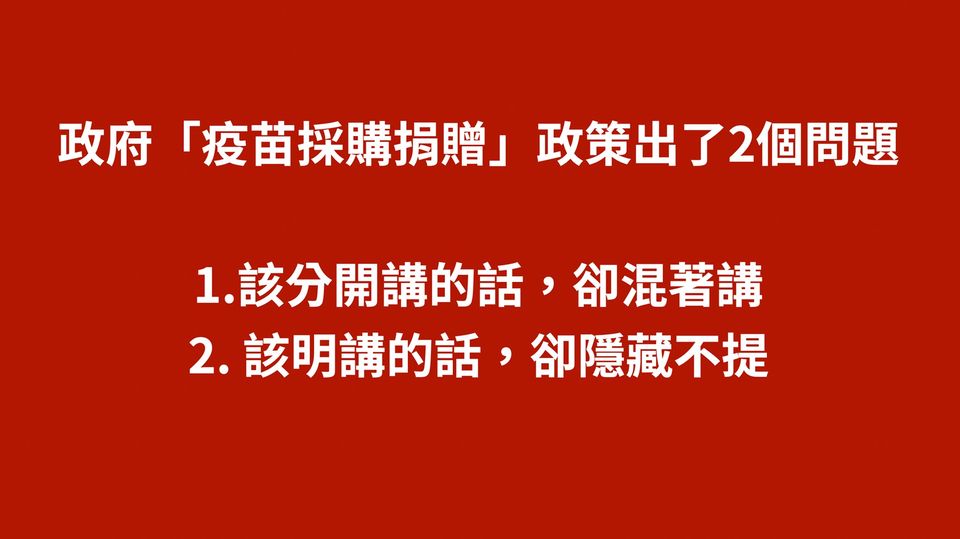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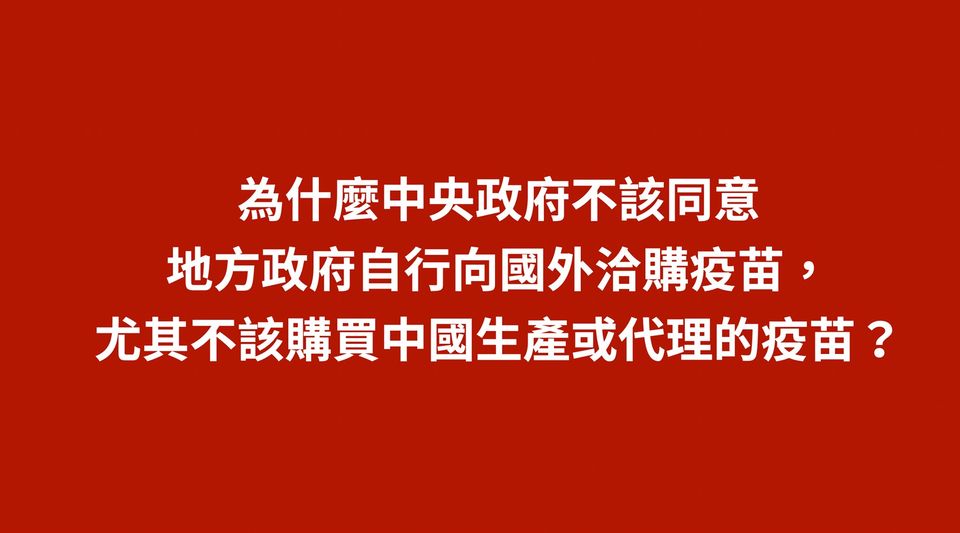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