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9月16日20:45
A 工作B 閱讀C 出版L 人物O 活動與新聞報導
1.
2012 年,莫尼卡.巴倫可(Monica Barengo)即將在義大利杜林的歐洲設計學院(IED)畢業。畢業生都要提出作品集給評審委員過目。
莫尼卡.巴倫可雖然從小就熱愛繪畫,也一直透過圖像尋找表達自己的方式,也即將在這所名校畢業,但是日後她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有些低落,因為原本讓她覺得能夠闖出一片天地的校園泡泡就要破裂,「而我即將面對自己永遠無法成功的現實世界。」
不過,第二天她收到一封電子郵件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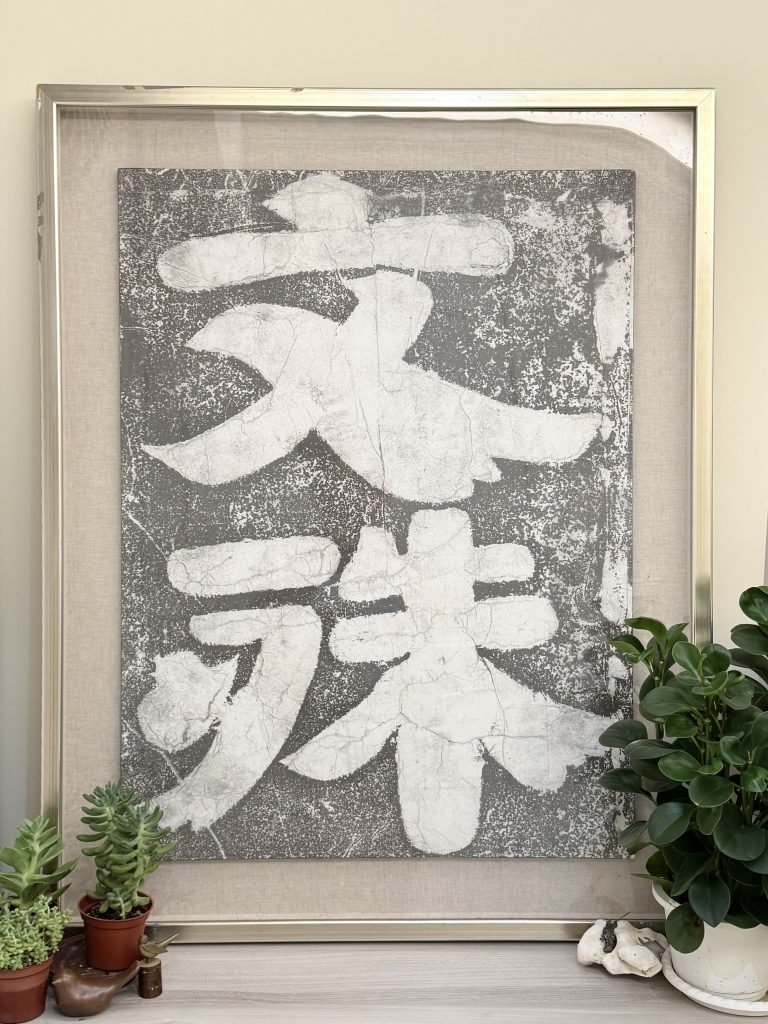




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