與兩位貴人重逢
E 人生回顧P 隨筆
1979年我拋棄了韓國居留權,孤注一擲地回到台灣。窩在分租的房間裡,找不到工作,一文不名地靠朋友接濟。每天早上醒來,看太陽從東方升起,傍晚看太陽西下。一天天重複。名叫鄭麗淑的房東和我比較熟了之後,說要幫我介紹些翻譯的工作做。我的生命從此有了新的開始。多年後,我很幸運地和鄭麗淑重逢了。
1979年,我的房東鄭麗淑在台灣一家雜誌社上班。當時正在擴展的長橋出版社老闆鄧維楨先生常去聊天,有天鄭麗淑回來說他們需要特約翻譯人員,鼓勵我去試試。我去見長橋另一位老闆劉君業先生。劉先生給了我生平第一個工作,還特准我可以去使用他們的辦公桌。劉先生後來出國。三十一年後,我和他今晚重逢。
4月8日晚上,我和我生命中的兩位貴人相遇。照片裡的女士,就是1979年,在我最落魄的低潮,幫我介紹找到生平第一個工作的房東鄭麗淑。坐在中間的這位先生,就是當年長橋出版社兩位老闆之一的劉君業,他給了我生平第一個工作,把我帶進出版業。
大塊的生日
E 人生回顧P 隨筆
今天是大塊的生日。
附一張1996年10月30日發表第一批四本書的記者會照片。

最左邊是《豺狼的微笑》作者蔡志忠。其左手邊是提供我們《福爾摩啥》出版及編輯建議的魏延年。再來是我。我左手邊是台灣英特爾公司的總經理,代表英特爾總裁Andy Grove所寫的《十倍速時代》。再過來是Peggy, 她的作品是《Peggy來占星﹣愛情魔法書》。
離開時報後,蔡志忠第一時間說要支持我一本書,後來就是《豺狼的微笑》。
稍後,我在那年的美國書展BEA上買了Andy Grove的自傳。後來把“唯偏執狂得以存活”的原書名改為《十倍速時代》。
大約那同時,我和兩位久住台灣的法國朋友魏延年和施蘭芳聊天,得知有《福爾摩啥》這麼一本奇書,決定出版,請薛絢翻譯。
Peggy這位讀大氣物理的年輕美麗的小姐,從沒出過書,是我們當時的秘密武器。《Peggy來占星﹣愛情魔法書》裡附了一片磁片,內有可算出星座命盤的程式。在網路還不發達的當年,算是創舉。
大塊靠這四本書開始揚帆啟航。
感謝這些年來所有支持我們的作者,和共同努力的同仁。
換一個擁抱的姿勢
E 人生回顧F 文化相關G 政府與政治
本文同時刊載於08.09.19《中國時報》。這裡的文字略有調整。
我十八歲從韓國來台北。那天晚上,飛機到了台北,出了松山機場,外面天黑黑的,下著雨。有一個朋友的姐夫來接他,問我有沒有人接,我說沒有,他們就邀我去他家住一晚,第二天再送我去學校宿舍。
我的台灣記憶就是這樣開始的。那個一切都未知,未知裡有黑暗,黑暗中卻充滿著各種可能的印象,是永不會消失的。
一九八七年,我在松山機場附近上班。冬天的台北,早晨上班等在紅綠燈口的時候,抬頭看到的天空雖然是灰濛濛的,但卻可以感受到臉頰為之微微發麻的震動。解嚴前後,台灣的空氣之中,充滿著可以實質感受到的震動。
一九九○年,我去中國大陸出差。回來的時候,迫不及待地想知道,出國之前鬧得不可開交的國民黨主流與非主流之爭,有什麼最新發展。偏偏一路就是沒有台灣報紙可看,勉強拿起香港報紙來翻翻,看不到什麼相關新聞,但是等飛機一落桃園機場,就知道從報紙到電視,從大街小巷到計程車,沒有人不在繼續為政治熱加溫。
我那是第一次體會到,台灣幾十年的政治禁忌打開之後,像是開閘的洩洪,不可能在幾年之內停止。而大眾媒體基於為「大眾」的興趣服務,難以不為政治熱加溫。但,那也是window 3.0風光登場,微軟才剛要開始改變這個世界的時候。所以想到身為書籍的出版者,可以,也應該避開一些大眾話題,以政治熱之外,政治熱之後的議題,為讀者做點事情。於是我出版了一個Next系列。
我的心底,一直在好奇,台灣的政治熱到底會燃燒多久。到底什麼時候我們才會邁出這個政治熱,而進入下一個階段?五年過去了,十年過去了,四周絲毫沒有任何停止的跡象。政治熱仍然在到處都燃燒得很歡。即使是今年的總統大選也仍然如此。
所以前一陣子,有天中午和朋友吃午飯的時候,倒突然有個感受。
談論著最近不論大家是屬於哪一個陣營,都為政治人物的種種而感到失望、疲累、無力,我頭一次覺得等待了快二十年的答案,終於浮出來了。任何事情,都不會發生得沒有另一面的意義。大家為政治人物的種種而感到失望、疲累、無力的時候,也是政治熱可以開始降溫的時候了。
在我自己的心裡,倒把今年,二○○八年,和一九八七年那個感覺到空氣中有震動的台北連繫到一起了。我跟朋友說,「今年才是我們的解嚴元年吧。過去二十年,不過是『後戒嚴』的二十年。」過去二十年說是「後戒嚴」,因為太多人為之燃燒的熱情、借用的工具、偽裝的外衣,都仍然是取之於「戒嚴」。而只有當這些延續自「戒嚴」的熱情、工具、外衣都耗用到難以繼續使用的現在,我們才可能真正開始準備進入「解嚴」的時代。
就算從一九五○年算起台灣也「戒嚴」了四十年。如果我們才只花二十年就能渡過「後戒嚴」的階段,那是很快的一段時間。
朋友看我說得開心,就問我自己準備怎麼開始面對這個新的階段。
我把十八歲來台北的那個晚上的感覺說了一遍。我還是覺得我看到的是一個天黑黑,下著雨的晚上。但是未知裡有黑暗,黑暗中又充滿著各種可能。
我回答他:「我還真不知道要怎麼擁抱這種可能,但是我知道一定要改變我的擁抱姿勢就是了。」
也因此,把這段對話記了下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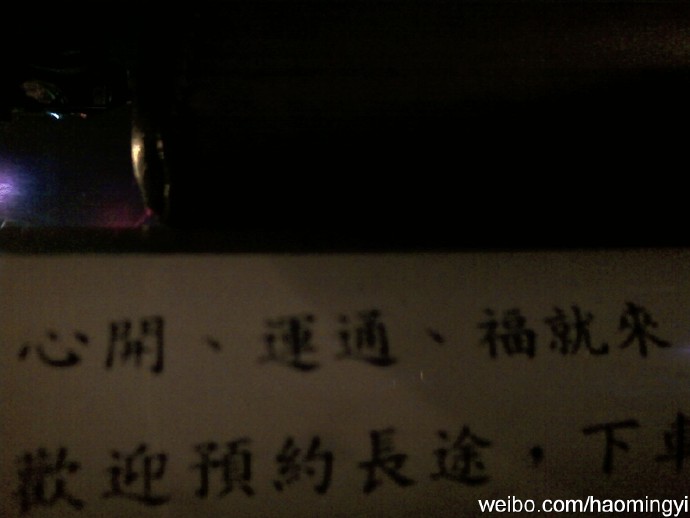
Recent Comment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