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,白建宇演奏貝多芬鋼琴奏鳴曲的第四天,我在臺中國家歌劇院出了一個奇異的狀況。後來,我不怕見笑,把經過及背景寫了一篇文章,發表在歌劇院昨天出刊的《大劇報》上。以下是該文,原題「Music is the Pure State of Mind 白建宇帶來的貝多芬震撼與寧靜」,也再次向貝多芬和白建宇致謝。
六年前的四月,我在焦元溥的介紹下,認識了白建宇和他的太太尹靜姬。
尹靜姬,是從1960年代起就在韓國家喻戶曉的超級巨星。婚後淡出銀幕,仍然保持「國民演員」的地位。所以開始的時候,我和她的話題比較多。尤其我在釜山住草梁洞,尹靜姬說她父親過去住釜山的時候也在草梁洞,算起來還有同鄉之緣。
韓國人有一種講究「態勢」的習慣,比較上年紀、有社會地位的人,越發矜持。白建宇夫婦是極少數打破我這種印象的人。他們兩人不但謙和,並且七十上下的人還有著說什麼做什麼都不經掩飾的童心,讓相處的人感到很自在。
這樣我們保持聯繫,每次白建宇來台,就聽他的演奏,也一起聚餐。
逐漸,因為音樂,我和他交談的時間也比尹靜姬更多起來。
◎
我聽古典樂並不多。
但是白建宇的演奏,很容易就讓人體會到他指下莫名的奇特力量。
聽他彈舒曼、李斯特,每次都讓我更想了解那些音樂家,讀他們的傳記;也比較許多演奏版本,想體會他的奇特何在。
他來演奏蕭邦那一次,我不在臺灣,沒趕上。但在那之前,白建宇送過我一張他彈的蕭邦的CD。其中 Rondo In F, Op. 14, “Krakowiak” 這一首,令我著迷。我寫信給白建宇,告訴他我非常肯定在開頭處看到了這麼一段影像:
「一個人像是在雪夜,又像是在春雨中,
像是在你視線剛好所及之處,又像是剛好模糊之處,
眼中帶著像是微笑,又像是淚影,
像是送你千里遠行,又像是在迎接你三十年返鄉。」
◎
因此,三年前,聽說白建宇要在首爾演奏全本貝多芬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,我沒有考慮,就和焦元溥一起去聽了。
白建宇說他到六十歲才覺得自己懂得貝多芬,錄了所有鋼琴奏鳴曲的CD;2007年首度現場連續演奏後,那次是事隔十年後再次嘗試。
我很慶幸做了那個決定。在首爾住了八天,每天晚上聽白建宇把貝多芬復活,結束後跟他一起去吃宵夜,也啟發了我對貝多芬的興趣。
首爾演奏最難忘的,是最後兩天。一天的焦點是第29號 Hammerklavier(槌子鍵琴大奏鳴曲),第二天是渾然天成的第30、31、32號連奏。
聽過第29號的晚上,我在筆記上寫著:「今晚白建宇彈得轟轟然。也體會到貝多芬打破打破打破打破一切的創造力和生命力。生命就是不受任何拘束,也不讓任何人揣測、追趕!」
我充分浸泡在貝多芬的魅力,也是白建宇的魅力之中,迫不及待地讀貝多芬的傳記,動手整理他的作品年表,也丟給自己一個巨大的問號:「有沒有可能再聽到這麼神奇的演奏呢?」
這樣,得知臺中國家歌劇院總監邱瑗要在2020年貝多芬誕生250周年之際,邀請白建宇來演奏全本貝多芬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之後,我開始了倒數的等待日子。
◎
2020年12月再見到白建宇,感慨當然很多。
多年來一直陪著他在全球各地演奏的尹靜姬,患上艾滋海默症,情況越來越惡化。 我最後一次見到她,是在巴黎。雪夜中,白建宇把她先送上計程車,回首揮別的身影,難以磨滅。
而這次再看到白建宇,除了2020本身是如此多事之一年,加上他旅途中只剩獨身一人的巨大變化,我毫無懸念地相信他再次連續演奏貝多芬,必定會有巨大的不同。
我自己這三年間對生命的認識,也有變化。所以我也相信自己身為聽者會大有不同。
只是,沒想到到底會有多大。
◎
無意中,很幸運地,我訂了和白建宇同一家飯店,每天會有段早餐談話的時間。
我先注意到他對練習的重視。
白建宇來臺後,先在邱瑗幫他備有鋼琴的隔離處練習了兩個星期。期滿出關,他直奔臺中繼續。周間晚上每天的演奏是晚上七點半開始,他就早上十點前出發。周末兩天是下午三點開始,他更是只吃到八點五十分就要去歌劇院練習。
我好奇他怎麼連十分鐘都計較。
那十分鐘的計較,出自於他對貝多芬的讚嘆。白建宇說,不像莫札特的鋼琴作品良莠不齊,貝多芬的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每一首都是傑作,每一首都有自己獨立的生命,但三十二首又相呼互應,合為一體。因此他把這八天的演奏當成巨大的挑戰,也想知道自己在首爾之後三年沒碰這些曲子,這次會彈出什麼。他說練習時間不夠,每一分鐘都要搶。
每天我也記一些他的感觸。
白建宇說,今天很多彈鋼琴的人,技法無可挑剔,但他們只是彈在琴鍵上(play on it),而沒有彈進鋼琴裡(play into it)。只有彈進鋼琴裡的時候,才會知道那是有生命的,是會回應你的。
「也不只鋼琴。任何物件都有生命,只看你如何對待。」他跟我說。「這個杯子也是。」
之前我聽他說過鋼琴在不同的調音師手下如何顯出不同的生命,而他一生遇上調到滿意的鋼琴次數也數不滿一隻手。但是他對鋼琴,對物件有如此體認,更加深我的好奇。
受了這些影響,我幾乎每場都提前半小時入場,以逐漸形成儀式般的程序,讓自己在座位上調好最適合的坐姿,也準備好聆聽的心情。
國家歌劇院八百多人的中劇院,為鋼琴演奏提供了頂級的音場。我坐在第一排的輪椅席,正好在鋼琴的對面,就更不想讓自己的聽覺遭到任何干擾和浪費。所以八場我每一場都是從開始就閉上眼睛,直到結束。我使用平日禪坐的方法,把一切念頭放下,只讓自己浸入琴聲之中。
雖然我還是很外行,但希望成為一個全心投入的聆聽者,來回報也回應一位全心投入的演奏者。
◎
從第一天起,就有人為白建宇的演奏感動到落淚。我看到網上有人說了一句,大意是他雖然沒看過貝多芬彈自己寫的鋼琴奏鳴曲,但是白建宇讓他相信貝多芬當年的演奏就應該是如此。
第二天的第8號《悲愴》,第三天的第26號《告別》更讓我看到許多人或是為之哽咽,抽泣,或是哭濕了口罩。
我都沒有哭。
不是我不感動。而是我覺得自己每天都好像陷在感動裡還來不及出來。每次白建宇出來謝幕的時候,我心裡一直響著的是一句話:「怎麼可能這麼好!怎麼可能這麼好!」
我也在閉目聆聽中努力想聽出鋼琴自己的生命,像是在第三天他彈第六號的時候,也覺得好像真聽到了。突然,在很短的五六秒鐘之間,我聽到鋼琴亮出一段和前後都不同的聲音,像在暗黑中一道旋光騰身而過。
這樣,進入了第四天。
那天早上,白建宇跟我講了另一段話。
他說,這次他在彈的過程中,知道自己和三年前是很不一樣了。他也說不出是什麼。「我只能繼續全心全意地投入,讓自己保持一種「赤裸」(naked)的狀態,以便迎接任何新的可能。不過,這也會讓我處於危險之中。」他說。
我做了筆記,咀嚼了一會兒,有點不明白他這句話的意思。但來不及問,他已經趕著去練琴了。
◎
第四天的曲目,上半場是第16號, 和第17號《暴風雨》;下半場是第22號,和第23號《熱情》。
我照例做好準備,仔細看一遍焦元溥寫的簡介,做好進入音樂盛宴的準備。
在白建宇精心編整過的曲目下,加上中劇院無與倫比的音場,這一天上半場當然又把我的心情揚升到一個新的高度。
中場,我繼續靜坐,看到先是工作人員帶著設備,再白建宇進來,忙了一會兒把鋼琴挪動位置,更靠近舞台的立牆一些。
然後下半場開始。我又閉上眼睛。
也在那個下半場,白建宇讓我體會到什麼是貝多芬的鋼琴奏「鳴」曲。鏘然、轟然而來的琴音中,有一「鳴」驚人,有不平則「鳴」;有天籟自「鳴」,有金鐵交「鳴」;忽而排山倒海,忽而婉約低柔的鍵音,在敲打你,在叩問你,在環繞你,在釋放你,在壯大你,在隱約的極微點叮嚀你,在雄渾的開濶處震撼你。黑暗中,鋼琴端地在燦爛變身,那是弦樂、打擊樂,那也是鳴樂、聲樂,和一切你想像所及和想像不及的音聲。
結束後,全場先是靜默,再起立爆出掌聲和吼讚。
我的身體在發熱,心底有什麼在若隱若現地微微波動,而腦子裡想的反覆只有一句話:「這到底是什麼音樂?這到底是什麼音樂?這到底是什麼音樂?」
場中的觀眾逐漸散去。一如前幾天,幾位朋友過來,大家在交換彼此前所未有的感動和震撼。我想說什麼又說不出,繼續還是在思索:「這到底是什麼音樂?」
有一個人過來,在我的輪椅席旁邊的空位蹲下。我聽到她在唏唏嗦嗦地流淚,腦中又多了一句話:「這怎麼會哭呢?為什麼要哭呢?這麼美好的音樂!」心底那個波動起伏大了一些。
這時我聽到焦元溥在旁邊說了一句話:「從沒聽過這樣的《熱情》。」
熱情。對啊。這就是熱情啊。熱情啊。
我跟自己說著,然後心底的波動又大了一些,接著突然掀起一個巨浪,然後,我就在還有不少人的歌劇院的現場放聲大哭起來。
大哭。號淘大哭。事後再怎麼放大聲音也比擬不來的放聲大哭。
至少哭了三分鐘,我才有精神接過邱瑗遞給我的紙巾擦掉橫流涕泗。
第二天早上,我跟白建宇說:昨天我本來不懂他說的那句「赤裸」中會有危險是什麼意思,現在我懂了。聆聽到最赤裸的時候,一個六十四歲從未在這種公眾場合落淚的人,會放開一切顧忌縱聲大哭,確實也是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。
白建宇沒有正面回應我。他說,就像他所言,鋼琴是有生命的,前幾天彈得很好的鋼琴,昨天上半場卻狀態不對。所以他想到調動位置,讓鋼琴更靠近木質的立壁,希望借助聲音先撞上牆壁再反彈的力量來調整出不一樣的音場。然後他說了一句:「很多人問我音樂到底是什麼。我都回答:Music is the pure state of mind. (音樂是心靈的純淨狀態。)」
◎
臺中國家歌劇院的八天演奏結束後,我問白建宇接下來想做什麼。
他說:想彈一些過去沒彈的音樂,譬如 Chamber music. 但更重要的,是他想幫助一些年輕人。
白建宇是在1965年,十五歲的時候去紐約參加一場鋼琴比賽,雖然沒能得獎,但卻受到朱莉亞音樂學院的列汶夫人(Rosina Lhévinne)賞識,讓他留下來就學,不但沒收他學費,還幫助他爭取獎學金,從此開啟了白建宇先美國,再歐洲的音樂之路。
但二十五年之後,列汶夫人跟他透露了當年真正賞識他的,另有其人。
列汶夫人說,比賽期間,有一天白建宇在卡內基大廳練琴的時候,她和音樂家伯恩斯坦(Leonard Bernstein)匆匆在二樓穿廳而過。伯恩斯坦聽到白建宇的琴音,停下腳步,聽了兩三分鐘後,轉頭跟列汶夫人說:「你要注意這個孩子。你要照顧這個孩子。」
白建宇說,世界上彈鋼琴的有兩種人。一種是每個音符都彈得完美無瑕,但是卻沒有生命。另一種是雖然有瑕疵,但是其中有什麼。他想幫助年輕人一起探索那其中的有什麼。
「我從沒有想用音樂征服什麼。想的話我就不離開紐約了。」他說,「我一生都在想了解音樂是什麼,我想和年輕人一起分享。」
◎
白建宇也很愛攝影。去哪裡他都要拍,人、花草、蟲鳥、店面、空間。
在臺中的最後一天,我問他想去哪裡。他滑手機給我看他找到的照片。是高美濕地。
我和元溥一起陪他去了。
在風中,在沙流中,在海中,在夕陽中,他不斷地拍,不斷地說:「看看這個!看看這個!」
濕地有一些微小幾近難辨的奈米級螃蟹在蠕動,尤其吸引他彎身俯視。
我看著四周變化的光影,時間在飛閃而去的沙流中是安靜的,也是光亮的,一如他指下的貝多芬。
回來的時候,他說謝謝我們帶他去。
其實,是他帶我們去的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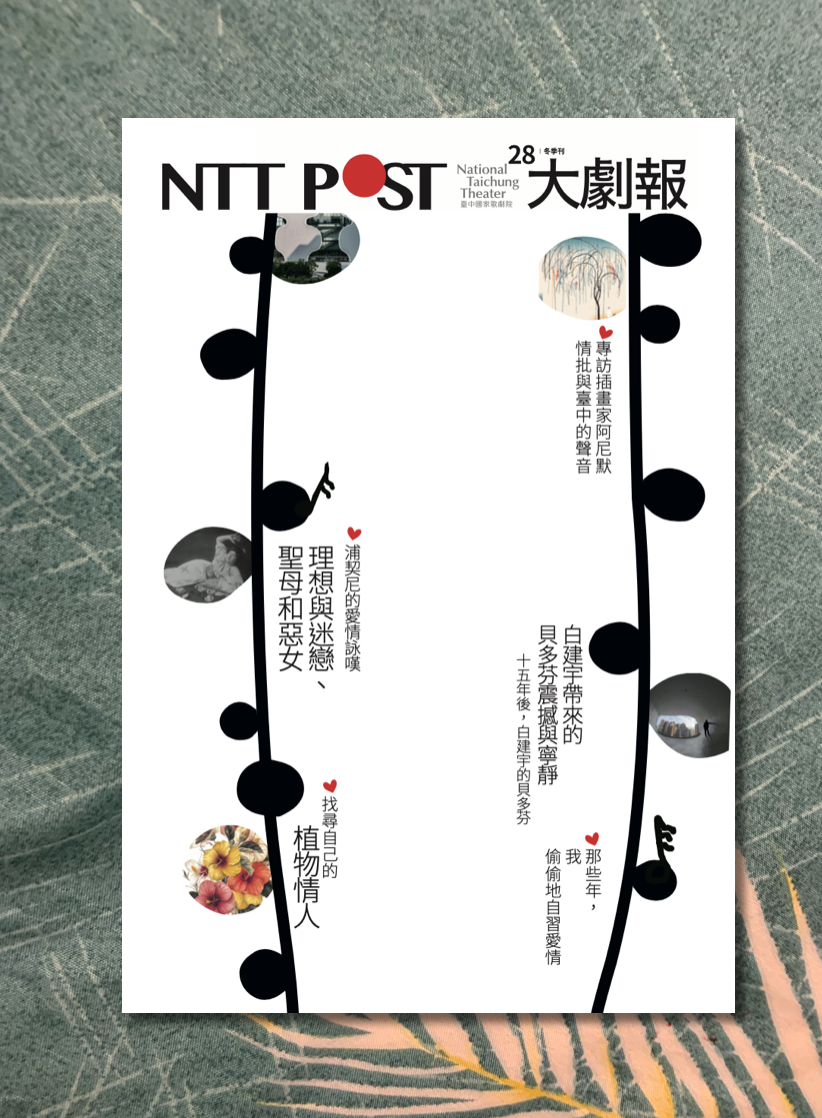
Recent Comments